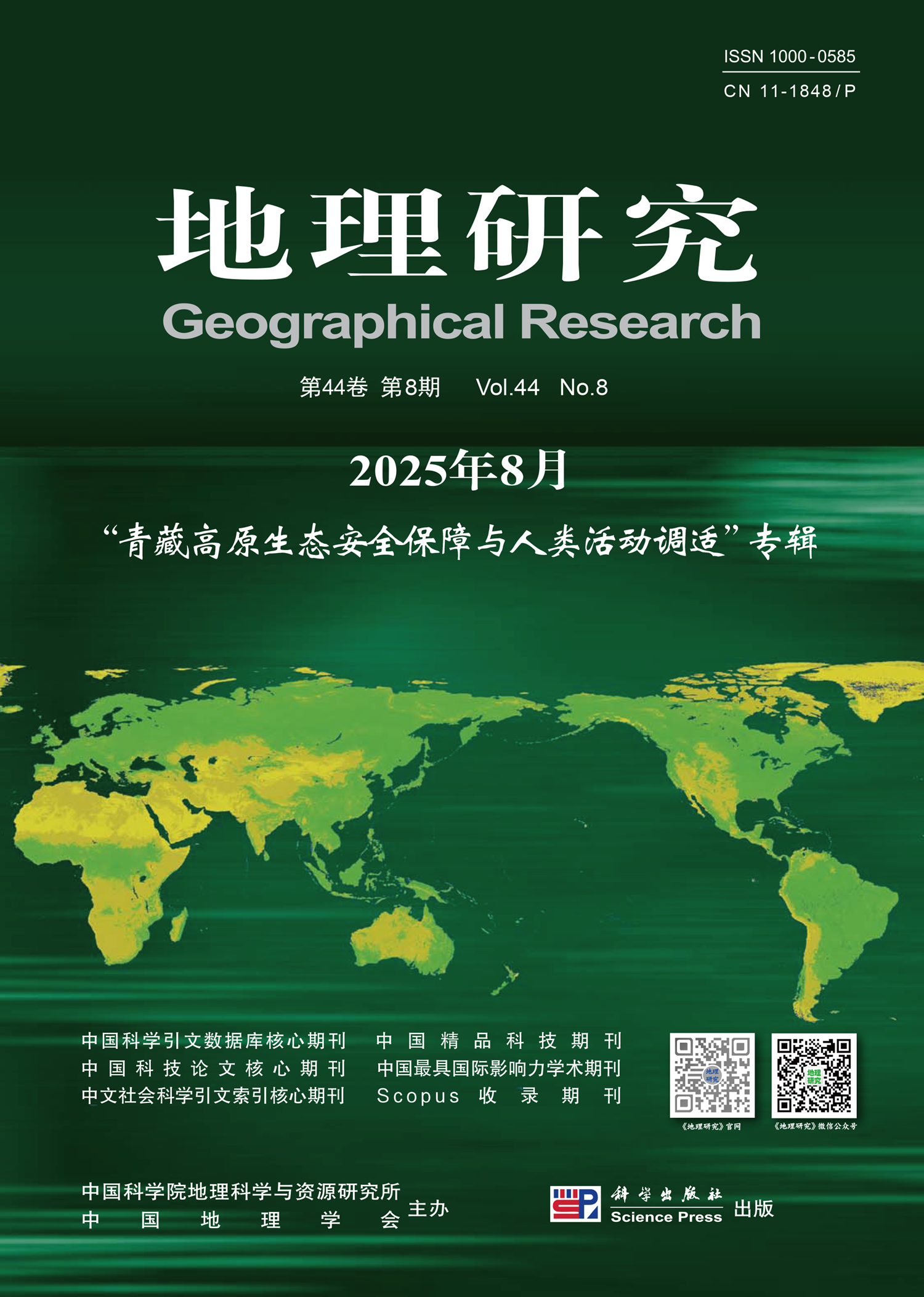
人口流动是改变青藏高原发展格局,构建可持续发展体系的核心要素。基于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分析青藏高原县域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演变特征,并深入对比县域人口流入、流出的影响机制差异。研究发现:① 青藏高原县域流动人口规模与活跃性显著提高,人口流动的地域类型从以非活跃型为主转变为以平衡活跃型为主、活跃净流出型为辅,县域整体流动活跃程度高达34.99%,青藏高原进入了人口流动活跃的“流动时代”。② 县域人口频繁流动主要发生于2010—2020年间,柴达木盆地、河湟谷地、一江两河地区形成了以高行政等级区域或主要工矿区县为核心的人口大量流入、少量流出的区域,和人口少量流入、大量流出的外围区县所构成的人口流动“核心-外围”的空间圈层结构。③ 青藏高原具备人口从经济相对欠发达县域流向相对发达县域的一般性规律,以及经济发展绝对水平较高的区县其人口流入率与流出率均较高的特殊性规律。但经济发展并非影响人口流动的唯一重要因素,行政等级对人口流入产生重要影响,自然条件如高海拔限制人口流出、耕地减少等显著推动了人口外流。
研究以跨越喜马拉雅山脉的边境通道为重点,遵循“类型划分-关键节点识别-方案集成”的思路,将14条边境通道划分为4种类型:国防安全与经济发展双重导向型、国防安全主导型、经济发展主导型和特色发展型。结合对西藏边境国防战略安全具有重要影响的30个关键节点乡镇,构建“战略支撑基地-关键节点-前沿支点”的边境通道建设体系。同时,结合318国道、219国道等交通干线,强化以地级城市为主的后方基地的横向联系以及后方基地与前方关键节点城镇及边境居民点的纵向联系,形成“一轴多通道”的梳状空间格局,并从开发模式和边境居民点布局等角度,提出分类引导边境通道建设的具体路径。
乡村空间转型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手段,对实现中国式乡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构建了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乡村空间转型分析框架,以互助土族自治县麻吉村为例,深入剖析了高原型乡村空间转型的逻辑过程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① 从行动者网络视角看,乡村空间转型是在政府和市场等多重力量共同作用下各行动者相互作用、协同演进不断推动乡村空间功能、结构和关系等发生重构、更新的渐进过程,异质行动者之间的博弈、分化和重组是其转型的核心推动力。② 麻吉村空间转型发展过程是不同行动者基于自身多元利益诉求和发展理念,通过主体性的互动和博弈在空间层面上的动态显现,呈现出由小农户经营主导模式过渡到乡村能人和村干部主导模式,再发展为多方主体合作与协同主导模式。空间转型经历了由内生稳定阶段到扩展生长阶段再到整合提升阶段的演进式发展,并形成以“高原农业+土族文化+生态旅游”为特色的空间转型路径。③ 关键行动者在麻吉村空间转型过程中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意图和目标,强制通行点由“以党建引领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转变为“生态与文化产业融合打造乡村振兴样板村”,返乡新农人和旅游开发公司逐渐成为关键行动者推动网络发生重构。④ 社会自发式力量积极对接政府政策安排并运用市场化手段调动社会力量参与麻吉村乡村建设过程中,行动者网络的动态调整与互动频率、非人类行动者的客观基础与自有属性、关键行动者的行动动机与利益目标、村民自身参与力度与受益程度等共同驱动麻吉村空间转型发展。
农牧区家庭能源转型已成为青藏高原人-地关系再适应的重要发展路径。依托第二次青藏高原科考项目,通过实地走访调研共获取1,591份家庭调查问卷,以此对高原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生计方式家庭能源转型现状及其综合效应进行了深入探究,并使用随机森林模型分析了家庭能源转型的关键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 整体来看,青藏高原农牧业家庭能源消费结构较为初级,煤炭与传统生物质能占比较高。其中,不同区域中的西藏地区家庭和不同民族中的汉族家庭能源转型水平较高。② 尽管农牧区家庭对初级生物质能的高度依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能源负担,但同时也增加了家庭室内空气污染的风险。能源转型水平较高的家庭,能源满意度也较高,且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明显。③ 家庭收入、海拔、家庭规模是影响高原农牧区家庭能源转型的关键因素,且不同驱动因素对能源转型的影响均呈现明显的非线性特征,能源阶梯理论、拐点理论等在青藏高原家庭能源转型研究中具有理论适用性。研究可为因地制宜、均衡发展、普惠共赢的转型政策设计提供理论依据,并将促进青藏高原能源系统绿色可持续发展。